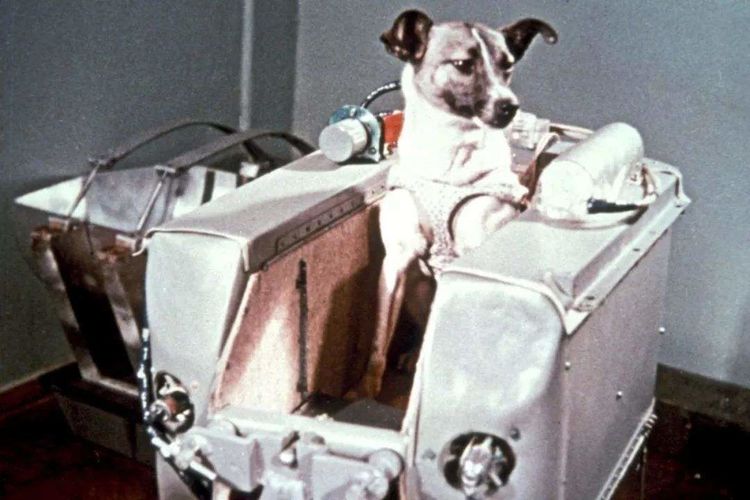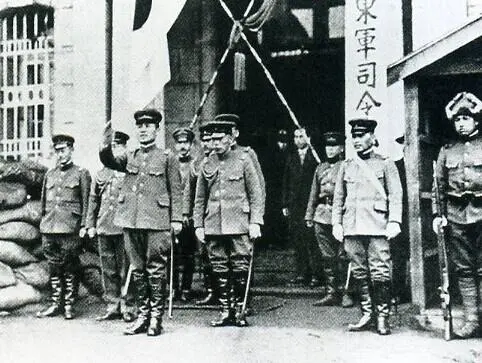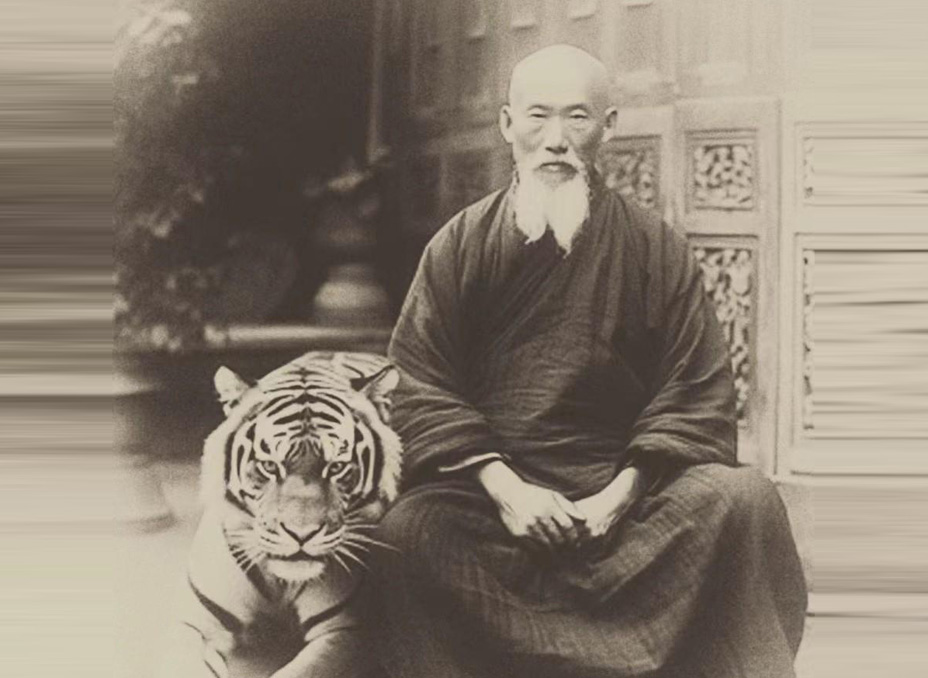今年春天我去拜访海德尔时,借来的录音机仍在他的阁楼里。我们中午吃了维也纳炸肉排和土豆,午餐后他告诉我:“米夏埃尔·赫尔曼是初审中唯一知道证据有什么问题的人。他说‘这不可能’,但他坐在原告方一侧!”
在民事案件接近尾声时,米夏埃尔有了另一个盟友。一位住在伦敦、名叫芭芭拉·齐普泽(Barbara Zipser)的德国学者在网上阅读了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米夏埃尔为弄清真相所做的努力。当年乌尔苏拉被绑架时,齐普泽还是个孩子,住在德国。她仍能回忆起当时感到的恐惧。我们今年见面时,她告诉我,就其影响而言,乌尔苏拉绑架案相当于德国的马德琳·麦卡恩案件(震惊世界的英国女孩麦卡恩失踪案件,译者注)。她说:“当时我想,不管是谁干的,我都希望那个人进监狱。”
齐普泽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分校语言分析专业,她能够运用现代分析技术来识别古希腊医学文本的作者。她决定将绑匪寄来的勒索信与海德尔在互联网上发布的马祖雷克的文字样本进行比较。齐普泽从用词和写作风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她说,写勒索信的人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故意用蹩脚的德语来伪装外国人的德国人。“我确定不是马祖雷克,”齐普泽这样告诉我。
她去德国见了米夏埃尔,并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一起查阅案卷,而后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她说:“我知道这难以置信,但我看到了证据,米夏埃尔已经做了非常出色的调查工作,我支持他的调查结果。”在刑事审判后的几年里,米夏埃尔认为马祖雷克仍然有50%的可能性是绑匪。现在他认为是1%。
2018年8月,民事诉讼结束,法院下令马祖雷克向米夏埃尔支付7000欧元的耳鸣赔偿费。这场胜利对米夏埃尔来说是个损失,因为要做出这一裁决,法官们首先需要与刑事法庭达成一致,认为马祖雷克与一个身份不明的同伙确实是绑架乌尔苏拉的人。
在致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媒体的公开信中,米夏埃尔写道:“我妹妹的死亡已经困扰了我37年,直到今天,仍不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难道实际上奥格斯堡的法律系统对解决乌尔苏拉·赫尔曼绑架案,也就是我妹妹的死不感兴趣?……如果法院决定盖棺定论,就应该充分意识到,不能把真相拒之门外。”
自2008年马祖雷克被捕以来,一直是瓦尔特·鲁巴赫(Walter Rubach)担任他的辩护律师。鲁巴赫是巴伐利亚州最著名的辩护律师之一,他的世界非黑即白。如果有客户问他是否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就像马祖雷克在2008年所做的那样),他会回避这个问题。鲁巴赫在奥格斯堡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会告诉他我不相信任何客户。我的工作是弄清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给他们定罪。”在马祖雷克的案件中,他从一开始就确信没有。
“很明显,马祖雷克是一个可能会犯下类似罪行的人。但没有确凿事实——这是一个最好的间接案例。”鲁巴赫说,“我仍然对他被定罪感到不解。在英国会怎么说?宁可让十个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也不要绞死一个无辜的人。”
尽管鲁巴赫与米夏埃尔私交甚少,但他一直在法庭对面看着他,欣赏且钦佩他。“作为共同原告,他所做的一切违背了法院的判决——这在德国从未发生过。”
在德国北部的监狱里,马祖雷克仍在试图洗清自己的罪名。今年我给他写了信,他回信说已经雇了私家侦探来追查2007年卖给他录音机的那个人。他写道:“我只是很生气,我即将迎来入狱11周年纪念日。”
四月一个温和的周日早晨,我在奥格斯堡见了米夏埃尔。就像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时间一样,他穿着休闲——运动鞋、蓝色牛仔裤和黑色夹克。尽管在法律上遇到了挫折,耳鸣也一直困扰着他,但他依然平静温暖,而且还保有幽默感。当我们驾车穿过巴伐利亚乡村前往埃兴时,他试图解释“超负荷”(他在1981年曾用这个词形容警方)的含义:“这意味你要做的任务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比如英国脱欧。”
米夏埃尔对案件材料了如指掌——他花在案件研究上的时间比任何辩方或控方律师都要长得多,所以比起亲属,他讲话时更像是个特别调查员,精准又客观。我们把车停在埃兴和雄多夫之间的路边,他注意到那可能就是绑匪把盒子带进森林时停的地方。一条越野车道通向森林。“我们需要走141米,”米夏埃尔说,而后看向左边20米远处,才找到乌尔苏拉被活埋的地方。他说:“我们不知道她是被麻醉后抬到那里,还是被迫走到那里的。但我们知道她是在专门穿过森林的小路上被带走的。”
几年前,米夏埃尔的父亲去世;2016年,他母亲从埃兴的家搬到奥格斯堡。但他弟弟汉内斯(Hannes)——那个冲浪爱好者仍住在埃兴的房子里。还有两名叙利亚难民租住在底层。米夏埃尔打电话给汉内斯(米夏埃尔不想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和记者一起出现在他家门口),汉内斯邀请我们进去喝咖啡。我们一直没提过乌尔苏拉。同他姐姐及母亲一样,汉内斯从未向媒体谈及妹妹的死亡。尽管米夏埃尔说,私下里,家人们、孩子们以及现任妻子都支持他调查妹妹的绑架案,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他是唯一一个要求重新审理此案的人。
 嗡在,分享新奇!
嗡在,分享新奇!